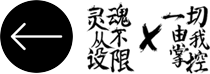吕文坚
著名独立乐队鼓手

羽果乐队坚果:游走在社会和乌托邦之间的鼓手
这个世界上打着“做音乐”的幌子无限期延长青春期的人实在太多,在他们当中,有些成为了崔健、罗大佑、李宗盛,剩下的99%不仅分不到一杯羹,反而搭上半辈子,却成为堂吉诃德。
在2002年,一个从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决心当一个全职音乐人,是一件注定不会讨好大众价值的事情。更何况,大众还包括了父母。
“你这是碗青春饭你知道吗?”,“你这天天不务正业的,大学算是白读了”,“所以你以后打算怎么样,你究竟有打算吗?”——父母有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在铁路上度过的,他们习惯了那种像火车准点抵达一样毫无悬念的生活。坚果无法向他们解释自己当时的状态——一种和朝九晚五完全相反的生活。
2002年,大学毕业,乐队正式组建。
在此之前,唱片公司几乎收割了所有音乐人的出场和收入,00年网络的突起,极大地打乱了唱片工业已有的流水线一样井井有条的布局,独立音乐人在低成本的创作和唱片市场的瓦解中野蛮生长——这恰恰就是羽果乐队的写实。

01-02年期间,他在南昌各个酒吧坐场,每个场子干两三个月,这批活在小城市的酒吧生命周期极短,坚果和主唱、贝斯手、吉他手一起过着又艰苦又快乐的日子。虽然听起来很不靠谱,却出乎意料地赶上了地下音乐的黄金时代——在一片反对声中,他每个月挣的钱是父母的三倍。
父母的铁路愿望自此彻底落空,账面上可观的数字让一部分反对销声匿迹,但无法让父母感到安心——这种频繁迁徙走穴的背后,是一碗彼此心知肚明的“青春饭”。
果然,这碗饭的热乎劲没能持续多久。
他喝了一口冰水,跟我说起了那些可以称得上“艰难”的时刻。就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帧帧在眼前晃过。
2001年,坚果和乐队伙伴们决定转型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专业音乐人,并将南昌作为日后一切音乐事业的起点。他们天天闭关,把自己锁在吉他手的屋子里,不间断地写歌、录音、刻CD,然后往北京所有唱片公司通发寄出——没有收到一个回复。唱片公司的地址都是通过最笨拙的办法,在网上一一查找的,在无法核实真假的情况下,很多CD都被退回来了——当时有多穷呢?他觉得幸亏退回来,不然亏大了。

2009年,他在上海的第四年,乐队发行了标志性唱片。并在全国24个城市的酒吧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出。
在西安快要上台之前因为食物中毒差点挂在宾馆里,不懂医的吉他手让他到医院买两瓶葡萄糖直接罐下去,然后勉强支撑着完成了整个演出——“在台上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死亡状态,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感觉四肢在潜意识地打鼓”。
在杭州演出期间,台下只有不到十个观众,安静得非常尴尬,人们的说话声甚至盖过了伴奏。
在广州演出期间因为被毒虫叮咬,很长一段时间内身体上都是流血的脓包,甚至就在各种状况的骚扰下,他还要频频打电话挽回女朋友——但是没有用,巡演一圈回到上海,他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手。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脸上一直带着笑,既温柔又讽刺。
后来总算熬到了“差点要红了”的时刻——

2007年,来到上海的第二年。羽果乐队作为受邀嘉宾,在经纪人的安排下前往北京参加音乐颁奖典礼。他在机场走出到达大厅的时候,几个彪形大汉一样的保镖前后夹护,将他护送到酒店。次日在工体举办的晚会,同场演出的都是重量级艺人。台下两三万观众的阵容让他感到非常恍惚,这让他们对此事恍惚至今。
在往届的草莓音乐节和迷笛音乐节上他也曾作为座上宾出席,演出时间从人数寥寥的中午两点钟,慢慢往前挪,从第一张发行专辑开始,十年来不断在创作——“我爸妈其实从来都听不到我们在唱什么,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会给身边的人介绍我们乐队,从南昌到上海,其实他们都是台下的观众之一”。
同年,李志的跨年演唱会座无虚席吸引了过万名观众,好妹妹乐队在北京工体的演出半个月内一切票务售罄,赵磊因《成都》走红,从音乐节舞台走到真人秀节目,在这些百里挑一的“个例”背后,无数音乐人与“走红”这一刻擦肩而过。
13-16年,他决定改变眼下的状态,以另一种姿势投入到生活中去——毕业后十多年,他第一次以职业人的身份走向社会,和今天数以万计的应届毕业生一样,为一份offer奔走。就像当年在父母的坚持下,他把高考志愿填上了“汉语言文学”,却在背地里做了四年乐队筹备,今天他和任何写字楼里任何一个上班族一样打卡下班,却走向距离公司将近一小时路程的练音房。他呆了五年,全公司都知道他工作只不过是为了做音乐。去年在羽果光阴浮尘演唱会上,他的老板带头买了一叠门票拉大队到现场去为他呐喊。
每一个独立音乐人的异军突起,都会被纳入文化现象的案例——然而在这些个例的背后,还有太多因为文化“新陈代谢”被过滤的人,他们从酒吧走来,从地下通道走来,从出租屋走来,没有对抗质疑的科班出身,也没有背景强硬的公司团队,每一次的试水都带着湿身的代价。
从坚果到羽果乐队,这十年来他们做的事情并没有太过出格的元素,所有的脱俗都带着妥协,但是这种挣扎太大众也太长久,反而让我们不太认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都在歌颂乌托邦,他却心甘情愿沾着灰把它建好。
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无数个堂吉诃德被现实的琐碎敲打,像塔罗牌一样倒下,终于成为了亿万个普通人的其中一员。而坚果撑过了一股又一股的推浪,从一个少年到一个中年人,他理想中的乌托邦直面过世俗的洗礼,挣脱过社会的标准,比起大红大紫的“一票难求”,更难的也许是每日日常里看不到跌宕的坚持。
羽果乐队曾经也叫晶体乐队,我问他,为什么换名字?
“希望我们的乐队能像一枚有羽翼的果实,至少和别的果实不一样”。
【Q&A】

凤凰青年:有没有一个特别想回去的时刻?
坚果:其实现在想想,如果我们能回到零三年或者一三年,再坚持一下下,赶到现在这个好时机。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坚持。
凤凰青年:你很坦白“工作都是为了养音乐”,有没有幻想过以后的日子?
坚果:09年的时候,第一次出国到西班牙去演出,“外面的世界”让我真切地了解到国外专业的创作状况和音乐文化。
其实我们最终的理想状态就是,靠着音乐到全世界去演出,然后赚了钱再继续创作继续演出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享受一个源源不断的过程。
其实我最初的想法是非常非常俗,就像那个谁啊,凤凰传奇啊,一首歌吃一辈子,上春晚,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就到处走秀就行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还是喜欢这种很自由的状态。我特别喜欢李健那首《贝加尔湖畔》,特别有画面感,特别美。
凤凰青年:全国巡演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辛酸的时刻吗?
坚果:经纪人带着我们四个人居无定所,他拎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里面塞满了我们的CD,他在现场卖。那个月是最艰苦的一个月,也是最快乐的一个月。
凤凰青年:演出期间最感动的时刻呢?
坚果:在郑州的时候,八点钟演出,七点钟开始下滂沱大雨,那个酒吧都淹到了,我当时都绝望了,心想完蛋了这场雨是完蛋了。结果有的歌迷是游过来的,就穿着泳裤在那里泡着水。当时来的人有六十多个人,很不容易啊,那么大的雨。当时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凤凰青年:你自己最满意的一首音乐是哪首?
坚果:《开往天堂的火车》 让我感觉就像一直在开往我向往的那个地方,一直开一直开,没有终点。

凤凰青年:现在的歌手特别是民谣歌手,他的走红是一夜之间的走红,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坚果:这就是媒体的影响力。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互联网,所以我们蛮羡慕现在这个时代的,收获很多,但同时也是来得快去得快。我的目标就是一直演下去,60岁红也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