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困惑,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快速增长的经济带来物质欲望的追逐,极速流动的信息让人在眼花缭乱中陷入空虚,不断出现的成功偶像又催促人跑步成为一个世俗的"成功者"。这世界每一天都变的比昨天多姿多彩,但春色如许,并未驱散后现代世界所迎来的一个又一个挑战。不过,历史的峰回路转中,总有一代人能够接续传统、坚守信仰、承担重任。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正慢慢走到台前,脚步沉稳谦和,抑或张扬个性。我们认为,成功,往往不是因为超越别人,而是由于战胜自我。我们追求生命的饱满,追求精神的丰盈,我们有自己的价值砝码,并愿意为微小的理想而行动。"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我们这群人和任何一代人都不同,虽然年轻,但是却充满力量。世道浮沉、革故鼎新之际,年轻人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这个国家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正因此,这个国家充满希望。

李理:保护动物是为了不让绘画对象消失

李理
自建动物保护站
在三年级时,北京孩子李理曾在作文课上发言:"我有三个理想,第一是当农民,第二是当动物园的饲养员,第三是当个画画的。"每个人都曾有过各式各样的理想,在成年后逐渐成为淡忘的记忆,可李理却将这些理想都变成了现实。
六岁拜师学国画,十岁举办个人画展,保送西安美院… 2000年,外界眼中的天才少年李理却做出了一个让人诧异的决定:退学,成立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那一年,他与几个小伙伴提着装满宣传页的编织袋,乘着火车和长途大巴,在北京周边郊县给老乡普及动物保护法,一做就是十几年。
今年四月,由保护站重点执行的黑鹳保护项目得到了由国家林业局颁发的中国黑鹳之乡资质,在延庆的候鸟迁徙保护区也由县级上升为国家级保护区。未来,李理还希望用水墨画的形式将中国NGO的野外保护行动介绍给国际专家。近期,李理与凤凰网分享了保护站成立至今所遭遇的种种波折挑战,以及十几年来支持他将动物保护事业坚持下去的动力。
不想让绘画的对象消失
凤凰网:在18岁这样一个年龄决定建立黑豹动物保护站,当时是怎样想的?
李理:我是一个画画的,作为一个画者,不想让我绘画的对象消失,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我出生在北京二环外、三环内一个叫中顶村的地方,是一个城乡结合部。那里的环境非常感染我,有很多树林、大野地,也有很多野生动物陪伴我。我也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喜欢玩变形金刚这样的玩具,我就特别喜欢在大野地里玩,看蝌蚪的孵化过程,藏在树上看大鸟喂小鸟,那里一直都是我童年的乐土。
后来二环以外城市扩建,不断地拆迁,村庄里一片片的土地都变成了胡同,我的乐土没了。这一点启发了我,人失去了玩的地方,动物的生存空间也被挤压,我从那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个动物保护者,不让我绘画的对象消失。
凤凰网: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城市化,自然被人工的东西逐渐取代,对您来说这一切有怎样独特的意义?
李理:我原来玩的地方盖了许多厂房,拆迁之后很多工地垃圾,瓷砖、塑料袋逐渐填满了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池塘。那附近有一个洼地,原先是一片芦苇荡,开着荷花、睡莲,深秋时还有天鹅。后来由于垃圾越来越多,家家户户都往那里推渣土,这里就变成了脏乱差的地方,所有的大杨树都被砍掉了,等到最后一棵死掉的树的枝头挂满塑料袋的时候,那种形象特别感染我。
从那时起我就觉得,一定要行动起来,成立一个保护的组织,但我不知道怎么做。当时我还在西安美术附中念书,准备保送西安美院。上美院的时候我也发现,艺术的创作是需要对象的,不能依照标本来画画。在美院的时候我们经常画一些雉鸡的标本,我不想画标本,想画那些活的(动物),也经常逃课出去画画。我觉得画画固然很重要,但人的生存环境,在野生动物的陪伴下一起长大的空间没有了,我应该做点什么。所以我离开了美院,开始从事保护行业。

开始几乎没有资金注入
凤凰网:从2000年开始做动物保护站,有碰到过哪些困难?比如资金问题怎么解决?
李理:从事保护活动一开始是非专业的,2000年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后来2005年的时候我拉起了12个人左右,五年下来看到了很多不好的方面。比如说资金从哪里来?我的交通工具、考察工具都需要资金。一开始非常困难,因为几乎没有资金注入。就是几个小伙伴拿压岁钱,我也不想伤了朋友的和气,一般是我来拿。我们的书包是编织袋扎了根旧皮带,用来装海报宣传页,身穿50块一身的迷彩服,脚踏8块钱一双的旧胶鞋。在沼泽里巡护时一脚踩下去,再提起来时鞋还在烂泥塘里,最后索性光了脚在泥地里走。所以那时很艰难,我们没有车辆,只能坐火车、坐长途车拎了一些东西去宣传。
在野外巡护的时候发现(动物)珍品,老百姓也不太理解,觉得你们这些城市里的孩子不好好读书,为什么要在山沟沟里发这些保护法、明信片?一开始跟老乡也有过一些冲突,因为野生动物和当地人之间也有一些矛盾,比如野猪拱地、猴子偷吃农民家的果子等。家人也不理解,觉得18岁毕业后应该找一些稳定的工作。我的小伙伴、同学们也不理解。
2005年因为没有资金,保护站曾面临解体。有一年大雪,我们团队发传单来到在一个峡谷深处,四处一片漆黑,只有一堆火。我们只有简单的帐篷,还是漏的,连睡袋也没有,喝的水也已经冻成冰,要烧开才能喝。看着朋友们睡不着觉,只能围着火烤手心、脚心取暖,头顶、肩膀上都是花掉的雪,还在冒着烟。虽然对搞美术的人来说,这是个很美的画面,应该把它画下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特别凄凉,我为什么要带着好朋友来大山受这个罪?这是我唯一一次有了想放弃的念头。
凤凰网:为什么又坚持下来了?
李理:这时我感觉到左边或右边山谷深处传来大猫头鹰"哼呼""哼呼"地叫声,我能联想到这个声音传到对面的崖壁上再弹回来,回荡在峡谷里面。大家静静地听着火嘎嘣嘎嘣的响声,这一点打动了我:我为什么要带着他们来这里?因为搞音乐的还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搞美术的人还能看到这样的画面,其他人还能感受到这样与动物的共生,所以我没有放弃。回到城市后,很多人就开始离队了,12个人只剩下2个,我也觉得很难受。当时政府政策并没有往这边,大的NGO觉得我们太小,应该去上学,学了相关知识以后再来搞这个。
开画廊盘活保护站
凤凰网:其他小伙伴都离开了,你后来是怎么解决资金问题的?
李理:2005年当大家都离队了,我就感觉到资金很重要。我觉得我要开始卖画了。我当时社会经验比较少,只会画画,就想到开画廊,用这种方法来淘金。
凤凰网:生意好吗?
李理:没想到生意还挺好。画廊开在马莲道,北京喝茶的一个地方。喝茶的人都比较喜欢字画,就歪打正着了。我卖了很多字画,换到了充足的资金,一边看店、一边做保护、一边画画。我买了几辆车,很多设备,包括录像机、监测设备、摄像机,后来发现数码的时代到了,又换掉买了大的摄像机和单反。
为什么要买这些设备?因为保护野生动物需要很多证据、资料,但2005年-2007年我发现很多朋友不会使用这些设备,比如说GPS跟踪系统,卫星遥感系统,还有远红外线。就这么巧,在2007年4月份,我认识了我的老师解焱。他当时是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项目的主任,在64个国家展开工作。由于我们做的工作不像那些俱乐部,后者只是随意聚在一起看看鸟。他看到了我们的这种精神,跟纽约那里是一样的,是真正扎在大山里生活来从事野生动物保护。我们跟他们很吻合,但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他就说,"没关系,我们把你们吸收进大组织下面进行学习,无论是从事鸟类保护的,两栖类,猛禽的,还是兽类的,都去上课。"
被组织收编进正规军
凤凰网:所以后来那两年都是在国外上课?
李理:实际这两年都是他(解焱)带着我们跑野外,在四川做林鸟密度调查,做各种各样的考试,回来以后我们都成了半专业式的野保人士。我的老师是在东北和西部做野生动物保护,东北的东北虎,西部的藏羚羊、熊,华南的扬子鳄。所以在学完两年后,老师就把我们发到他的项目上去,进行项目学习,在这些大项目点上看老外是如何做的。我的老师就按照NGO领导者的目标在塑造我,如何领导自己的团队,如何进取,发挥整个团队的整体效益,读了很多从东南亚翻译过来的书。到2009年,保护站已经成为一个正儿八经的组织了。卫星遥感、海事卫星这些设备都会使了,应用上藏羚羊、东北虎的追踪上。我的老师就觉得,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野保员了。
凤凰网:被国际组织吸收后你们的资金来源是否有拓宽?
李理:是这样的,保护站是可以划为纽约站的下属支队,从事学习,但由于纽约是专款专用,不能让资金流入到我这边,所以我的资金是一国两制的那种感觉。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虽然他也看到我们的资金不太多,但纽约还是花了很多费用来培训我们,包括我们飞去全国各地上学、考试的机票和住宿。其他的资金都是我的卖画所得。
凤凰网:是否有计算过你在动物保护上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李理:那天我算了一下,大概到现在有400多万吧。
凤凰网:坚持那么多年做一件事,你觉得你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李理:咱们这代人老有一种想干点什么事的念头,看到一些不对的事老想扭转过来。老想打抱不平也好,想真心真意地来做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就像我在书中写的,在人生中最年轻的岁月来奉献给动物保护事业,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
后记:
从理想到现实,有时候只有一步之遥。而将理想变为现实,却需要自我不断的努力和坚守。李理用十几年的时间实现了一个梦想,在放弃了许多常人看来更简单也更符合常理的人生路径后,他找到了最让自己幸福的那一种选择,那种真心真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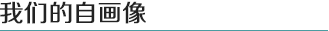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