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困惑,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快速增长的经济带来物质欲望的追逐,极速流动的信息让人在眼花缭乱中陷入空虚,不断出现的成功偶像又催促人跑步成为一个世俗的"成功者"。这世界每一天都变的比昨天多姿多彩,但春色如许,并未驱散后现代世界所迎来的一个又一个挑战。不过,历史的峰回路转中,总有一代人能够接续传统、坚守信仰、承担重任。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正慢慢走到台前,脚步沉稳谦和,抑或张扬个性。我们认为,成功,往往不是因为超越别人,而是由于战胜自我。我们追求生命的饱满,追求精神的丰盈,我们有自己的价值砝码,并愿意为微小的理想而行动。"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我们这群人和任何一代人都不同,虽然年轻,但是却充满力量。世道浮沉、革故鼎新之际,年轻人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这个国家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正因此,这个国家充满希望。

毛晨雨:回乡种田的独立导演

毛晨雨
种田的导演
考上同济大学,应该是和建筑行业打一辈子交道了。然而毛晨雨却没有走上这么一条道路,反而是慢慢迷上了电影,并执意将电影变成自己的终生行业。2012年初,他回到湖南岳阳县老家种田,搞了一个"稻电影农场"计划。在别人眼里,这个回乡种田的纪录片导演有些另类,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1976年出生的毛晨雨和大部分同龄人看起来略有不同,他的身上有不少"地下电影导演"的印记,比如衣着简朴,略为不修边幅。更为独特的是,他带着一点神秘感。
"我父亲是湖南洞庭湖边上一位巫师。"古来巫医合一,这位巫医的孩子在学习上是村里最争气的。1996年,毛晨雨考上了同济大学混泥土结构检测专业。
考上同济大学,应该是和建筑行业打一辈子交道了。然而毛晨雨却没有走上这么一条道路,反而是慢慢迷上了电影,并执意将电影变成自己的终生行业。
2012年初,他回到了湖南岳阳县老家种田,同时搞了一个"稻电影农场"。一方面恢复传统农耕的习俗,另一方面,也将农耕过程拍成纪录片,在存放粮食的仓库放电影。
就这样,稻田与电影被这个回乡种田的独立导演谱写成了一曲悠远的田园诗歌。
行走的日子
相比建筑检测,工科毕业的毛晨雨更感兴趣的是电影。
大四时,他以几个同学为原型,拍了一部学生电影,叫《行走的日子》,主要讲述一个农村大学生在毕业时碰到的问题。文学、诗歌、电影,成为这批受到"后80年代"影响工科男生的理想国。
毕业后,原本可以去湖南建筑科学院做检测工程师的毛晨雨揣着梦想随着朋友去了北京,四个人组建了一个工作室。
不过由于能力不足,这个工作室不到一个月就宣布解散了。"我和其中一个朋友接了北京电视台对外部一个扶贫的节目,做了不到一年。后来有个朋友在山西又介绍了一部片子给我拍。但我没有拍成功,2002年初,也就是毕业一年多后,我又回到了上海。"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上海,毛晨雨却发现,上海并没有留给他太多拍电影的机会。
为了生存,他和朋友住在一起,开始给《新闻午报》写书评和影评,但收入甚微。"回上海的第一年,我一直住在每月400块的房子里,真是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即使是那种境况,我当时还在想怎么去写一个好的剧本。因为心里有一种更强烈的冲动,总觉得自己掌握了足够的电影资本,可以单独去做一个电影作品。"
到了2003年初,生活困窘的毛晨雨觉得几乎快没路了,只能到51job网站上疯狂点击,结果居然看到有一个地方招纪录片的编导。
"那是松江一个房地产老板想组建一个'真实电影'工作室,也就是纪录电影,想做出一些文化品味。他们很快就录用我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架发现了一部《黑暗传》,类似于上古史诗,可以去那里拍一部片子。"
毛晨雨说,《黑暗传》是中国人去世之后的一个仪式唱词。从三皇五帝开辟鸿蒙,到现代中间历代的历史变迁,同时带有民歌演绎色彩的类似《薅草锣鼓》的形式。
"高行健根据它写了一个戏剧叫《野人》,另外在他的获奖作品《灵山》里也描绘过。我去拍了这部片子也起名叫《灵山》。"这部玄妙的片子从诞生开始就拍得很艰难,也很难得到播出的机会,老板还曾想把《灵山》运作上院线,但毛晨雨说,这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窘迫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6年出现了转机,毛晨雨参加了上海的下河迷仓举办的"概念艺术节",一下子得了个最高奖。
因为这个机缘,他和下河迷仓的两位老板产生了联系。"2007年他们给了我们全年资金支持,还有200多平方米的工作空间,创建了一个叫做'矢量源'的实验室。"随后毛晨雨去了贵州,拍摄了一组实验性质的电影,叫做"第二文本"。
"我的第二文本是让文本和拍摄对象都开放。比如我要拍摄一个苗族村寨里的故事,剧情不是我设计的,而是由拍摄对象那一家人决定。他们的劳动怎么分工我们就按照他们的分工进行,对某个活动家里人有什么不同的态度我们也会完全按照他们的逻辑去纪录。这东西最后体现的就是一种文本无表达,也就是不管作为一个作者、导演,你有多么强大的写文本的实力和控制欲望,最后都要放弃。"毛晨雨说。

亚文化记录者
贯穿2007年全年的实验电影拍摄让毛晨雨受益深远。
"我们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有责任去记录老百姓中间如普通尘埃般容易被遗忘的历史。人的写作决定了人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决定人的存在。"毛晨雨说。
也可能是这段时间的拍摄太紧张,第二年他就大病一场,在这段时间里,他拍了一部较为轻松的片子《神衍像》,是关于他的家乡、他的父母亲,关于村落风土族群制度的。"里面讲到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话,十个字:'我在哪里,哪里就有历史'。"
2009年,这部《神衍像》被日本山形电影节选中,最终获得"亚洲新潮流单元"特别奖。
对于毛晨雨而言,目前的中国,独立电影需要做出澄清和梳理,而不是变成一种拥有道德优越感的设计。"我并不认为独立电影是一种姿态,可能是我比较狭隘,我觉得真正的中国独立电影是注意到生存状况,跟某种生存现实有关联的。因为我是这么走过来的,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在这样坚持着。"
对于这份自我坚持,毛晨雨认为从深层次考虑,是有些非理性的。考上研究生的姐姐也曾怀疑他做电影的条件不成立,因为他的家是农民家庭,读大学时还着欠债,并没有资金支持他做电影这么耗钱的工作,而且他选择的独立电影路径是一个很难生存的路径,在整个产业中也比较难得到认同。
"对于电影,我就是喜欢,真的喜欢,因为电影会给我一种梦幻的感觉。"纯粹热爱着电影的毛晨雨在历经十年电影人生涯后,于2012年做了一个亚文化类型的计划,叫"稻电影农场"。
农场就建在毛晨雨老家湖南岳阳县门前的那块稻田,是一个自然农耕的生态主义农场。从农场组建,到田地耕耘,毛晨雨都扛着摄像机拍摄了下来,同时,他也拍了一部与农场观念、乡土文化相关的现代电影,叫《生产传统》。
"我们越来越强调效率,导致耕作文化传统、乡村文化都淹没了。所以我想要回归到一种低效的生态生产,在农场里种植一种在湖南几乎被淘汰掉,几乎没有生存能力的洞庭红霑。"毛晨雨说。种植的洞庭红霑是上世纪50年代前后本地主流的稻种,后来逐渐被高产稳产的杂交稻、超级稻及农户私自种植的转基因稻所取代。
毛晨雨的目标是第一年种8亩,第二年扩展到70亩,第三年采用公司加农户、或农户加农户的方式进行生产,再通过淘宝等平台销售。"希望我这种不使用化肥农药的生态主义生产能提高利润,再通过经济利益吸引并改变其他农户的选择。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通过一个5年的计划把那里一百七、八十亩的稻田改造成不再依赖化肥农药,依然可以生存的生态。"
乡村"乌托邦"
在回乡种田这件事儿上,毛晨雨的父母并没有反对。
"我爸爸一直觉得我是在做电影的,他们也不觉得我在做什么不恰当的事情。我也努力让他们觉得做这样的事还是挺有意思的。"毛晨雨的妻子一如既往给了他很大的支持,还用她画画的专长画了一本现代版的《天工开物》,就是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图。
农场的近30亩地中,有毛晨雨家里的4亩多地,还有从乡亲那里盘活的不种的田地。这一年,完全用人工方式除害,也不添加任何有机肥料的洞庭红霑收成还不错,毛晨雨说,不少农户对这种方式是认同的,因为他们租种在给农户带来利益的同时,还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不少农户要求转让稻田给我们种植。"他说。
那一年的端午节,由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策划的"湘会"活动在稻电影农场举办,一批电影作者、策展人、电影研究者和批评家等聚集农场进行了一周的学术会议,还决定创办一本杂志《电影作者》。
在毛晨雨的计划中,农场还要建一个艺术仓库,把人民公社时期拆掉的两个废弃的土墙村庄改造成他的小影城供他拍摄;第二文本实验室也要进行扩建,建成专门的工作室、放映室、青年宿舍。"我有很多做当代艺术的朋友,很感兴趣我将如何把这样一种生态理念贯彻到地方。"
不过他经营的"稻电影农场"淘宝店中,标价588元和648元的"洞庭红霑"销售并不太好,反而是纯手工酿制的红霑原釀在最近有52件的销量。"我没法做一个商人。"毛晨雨有些气馁。
尽管没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但这不妨碍毛晨雨在独立电影这条小众道路上的前进脚步。
2013年,关于乡村社会60年来历史反思的《拥有,新中国农民战争:修辞学的正义》拍摄完成;2014年,在家里添丁进宝的同时,他对乡村社会的反思和建设的三部长片也即将全部完成。
在毛晨雨的农场中,他企图逆潮流恢复一种传统的劳作方式,精耕细作,低效但生态;在毛晨雨的电影中,他并不是在单纯地拍电影,而是将拍电影与乡村修复联系在了一起。
后记:
毛晨雨对于电影有一种近乎于执拗的坚持,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份坚持让他经常在不同的城市颠簸,让他为生计发愁,让他遇到旁人不理解的眼光。但也是这份看上去逆潮流的坚持,让他将自己的理想贯彻到底,亲手建起了"稻电影"农场这个心中的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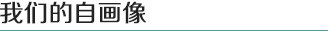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